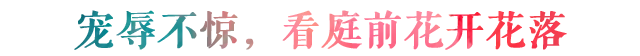二、《废都》的性爱描写与精英作家的精神还俗
《废都》性爱描写的大胆和直露,不仅在新时期,就是在整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小说不厌其烦地详述每次性行为的过程,从正常的性交到变态的口交都有。这对中国传统的审美阅读包括社会接受无疑是一种富有刺激性的挑战。
如此的描写有没有意义呢?
从文本的实际效果来看,不能说一点也没有。这主要就是:借此充分揭示“废都”之中知识分子的精神之“废”,写出他们在政治和商业两方面都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只好转向对性的变态追求,在放浪形骸、自暴自弃中实现自我消解。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抽去了这些性爱文字而代之以崇高的情爱描写,那么,这部作品有关知识分子精神颓败的揭示,能像现在这样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受;至少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主题思想。从艺术角度看,这样写也有助于扩大人物的私人化空间领域,给人以某种生命本真的感觉。
文学中的性爱是非常复杂的。性与美并非绝对对立。青年美学家潘知常指出:“从根本上讲,性与美是一致的,美的内涵就是性的内涵。这可以从人类的进化历史得到解释。就进化规律而言,个体的生存都是为了种族的繁衍,它通过否定自己来肯定种族的延续。美感正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而由大自然专设的奖励机制或曰诱惑,目的一旦达到,大自然就把这美感无情地收回,就像人一旦吃饱,进食的快感也就没有了……因此,承认性在审美活动中的正当地位,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一大功绩。而且人们还会有意识地利用‘性’,去消解传统的美。”
潘知常此述是有道理的。以大家熟知的麦当娜的裸舞为例,它就具有这样反传统的意义。1992年10月,她的《性·幻想·写真集》与唱片专辑《性爱宝典》同步发行。这天是星期二,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当年听到珍珠港事件的发生一样震动。麦当娜也自称:她这样做是为了改变人们对性的错误态度。还自称自己是一个性革命者,只有脱光衣服才感到自在。我们可以把她的初衷理解为对当代虚伪的审美文化现状的反叛。
对《废都》的有关性描写,我们也不妨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事实上,有些同志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才肯定了这部作品性描写的意义,没有将性简单排除在美之外。
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不加规约地将性的美学功能夸大,那就错了。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美不但有与性相同的一面(过去,这一面被忽视了),而且有与性不同的一面,或者说,有超出于性的一面。人类为自己所设立的美显然要高于性的美。而且,人类真正的美不是在完成自然的美的时刻,而是在完成价值的美的时刻。”同时还在于“人类已经使性从生理进入文化,从文化的角度讲,爱的越多,爱就可能越肤浅。像用剪刀剪一张纸,剪了一次,固然可以重新来过,但毕竟天地窄多了,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性的内涵应该是两重的,而且以其中文化的内涵更为根本。”还以麦当娜的作法为例,我们虽然对她的作法表示理解,但同时还要进一步叩问:她为什么要以如此惊世骇俗的姿态出现在当代社会?看来恐怕是一种犬儒精神在作怪:即“在价值虚无的社会,以抗拒虚无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一无所有,发展到自己也认为真是在抗拒虚无,以至达到一种自恋狂的境地……因此,她要求观众“审美的角度来看她的裸体,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一无所有状态,以此为审美,也只是掩饰美在身上早已不存在这样一个事实。”
《废都》中的性描写自不可与麦当娜的作法简单相提并论,但就性与美、性的生理内涵与文化内涵的关系问题上,彼此则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共通的经验教训。这里除了夸饰其笔、对主人公庄之蝶与唐宛儿、柳月、阿灿和牛月清四个女人的性爱关系投入了过分的热情,生理描写过于琐细外;主要是从中赋予的文化内涵比较单薄而缺少精神性的价值允诺,有时甚至成为一种简单的性宣泄,并流露了作者陈旧落后的性观念。如写庄之蝶对女人小脚的欣赏:“庄之蝶……看那脚时,见小巧玲戏,跗高得几乎和小腿没有过渡,脚心便十分空虚,能放下一枚杏子……嫩得如一节一节笋尖的趾头……庄之蝶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脚,差不多要长啸了!”类似的对女性肉体乃至生殖器欣赏、把玩的文字还有不少。另外,庄之蝶与几个女人关系,也几乎惊人地重复了古典小说中妻、妾、丫环的结构模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青年评论家蔡翔富有见解地将《废都》中的性爱描写,称之为知识精英开始“退出”了自我先锋的“角色规定”,“而复活了种种有关文人的传统记忆”,它使“作者回到了遥远的古代。在那里,他享受到文人的特权与荣耀,并进入文人的各种习性、癖好和游戏的生活方式之中,同时表现出男人的征服欲和对妇女的狎玩。”可见,问题不在于《废都》描写性爱,而是在于这种性爱描写本身所体现的观念是违反现代的,它丧失了应有的文化品格与艺术审美价值,内在地反映了精英作家在世纪末颓废思想影响下的“精神还俗”。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同样以大胆率真写性而著称的作家还有不少,如郁达夫、张贤亮、王安忆等。但他们只是把性当作一种文化的、生命的抑或道德的严肃思考对象,通
过性有关行为和故事的思考来实现文学的某种启蒙功能,其关注的重心是性的形而上的精神意蕴。无论是“五四”时的《沉沦》,还是80年代的《绿花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甚至更晚近的《妻妾成群》,在这些作品中,性是文化的,是一种道德。社会和审美的对象,负载着沉甸甸的内涵,而不是小说情节的一种调剂物。所以,在他们那里性描写无论怎样惊世骇俗,但都是极具理性和美学情致,并紧扣人物的个性和命运。这反映了作者精神上的高蹈,是与知识精英“导师”身分相吻合的。
与郁达夫、张贤亮不同,贾平凹却以相当非理性的态度对待性。他写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性关系,是通过知识分子“自恋”式的“名人效应”来叙述的。三位女性之所争相与庄之蝶发生肉体关系,主要就是因为庄是“名人”:唐宛儿羡慕庄之蝶的夫人“哪里尝过给粗俗男人作妻子的苦处”;柳月面对庄之蝶的书房则感慨地说:“让我看书,我是学不会个作家的。每日进来打扫卫生,我吸收这里空气也就够了”;阿灿在献身之后则幸福地说:“真的,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有你这么一个名人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这里,作者放纵笔墨,描写庄之蝶与几个女性之间沉酣于“爱河”之中穷情尽欲,与其说是违反现代性的一种虚假叙述(陈晓明因此将其说成是“‘名人欲’的假定满足”),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失去对社会和人类关怀激情之后的一种严重的精神虚脱。于是,他们只好醉入肉欲,半是夸张半是无奈地乞求于性事。正如庄之蝶所说:“终日浮浮躁躁,火火气气的,我真怀疑我要江郎才尽了,我要完了……身体也垮下来,连性功能都几乎要丧失了!……更令我感激的是,你接受了我的爱,我们在一起,我重新感觉到我又是个男人了,心里有涌动不已的激情,我觉得我并没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