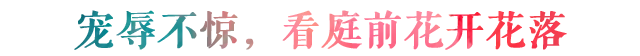西方人有一句名言说:不自由,毋宁死。这是说自由比生命还重要。但什么是自由呢?
就中国字义解释,由我作主的是自由,不由我作主的便是不自由。试问若事事不由我作主,那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价值可言?但若事事要由我作主,那样的人生,在外面形势上,实也不许可。在外面形势上不许可的事,而我们偏要如此做,那会使人生陷入罪恶。
所以西方人又说:自由自由,许多罪恶,将假汝之名以行。可知人生不获自由是苦痛,而尽要自由,又成为罪恶,则仍是一苦痛。然则那样的自由,才是我们所该要求的,而又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呢?换言之,人生自由之内容是什么,人生自由之分际在那里呢?我们该如何来获得我们应有的自由呢?
由我作主才算是自由,但我又究竟是什么呢?这一问题却转入到人生问题之深处。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曾把人之所自认为我者,分析为三类:
第一类,詹姆士称之为肉体我,此一我,尽人皆知。即此自顶至踵,六尺之躯,血肉之体之所谓我。人若没有了此六尺之躯,血肉之体,试问更于何处去觅我?但此我,却是颇不自由的。此我之一切,均属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即医学所研究的范围。生老病死,一切不由我作主。生,并不是我要生,乃是生了才有我;死,也不由我作主,死了便没有我,很少有人自作主要死。老与病,则是自生到死必由之过程,人都不想经由此过程,但物理生理规定着要人去经由此过程。
其他一切,亦大体不由我作主,如饥了便想吃,饱了便厌吃,乃至视听感觉,归入心理学范围内者,其实仍受物理、生理、医理的律令所支配。换言之,支配它的在外面,并不由他自作主。
佛家教义开始指点人,便着眼此一我。凡所谓生、老、病、死,视听感觉,其实何尝真有一我在那里作主。既没有作主的,便是没有我。所以说这我,只是一臭皮囊,只是地、水、风、火,四大皆空,那里有我在。因此佛家常说无我。既是连我且无,所以人生一切,全成为虚幻而不实。
第二类,詹姆士称之为社会我。人生便加进了社会,便和社会发生种种的关系。如他是我父,她是我母,我是他和她之子或女。这一种关系,都不由我作主。人谁能先选定了她自己的父与母,再决定了他自己之为男或女,而始投胎降生呢?那是我的家,那是我的乡,那是我的国,那是我的时代,这种种关系重大,决定我毕生命运。但试问,对我这般深切而重大的关系,又何尝经我自己选择,自己决定,自己作主呢?因此那一我,也可说是颇不自由的。
第三类,詹姆士称之为精神我。所谓精神我者,这即是心理上的我。我虽有此肉体,我虽投进社会和其他人发生种种关系,但仍必由内心自觉有一我,始才算得有我之存在。这在我内心所自觉其有之我,即詹姆士之所谓精神我。此我若论自由,该算得最自由了。因我自觉其有我,此乃纯出于我心之自觉,绝不是有谁在我心作主。若不是我心有此一自觉,谁也不会觉到在我心中有如此这般的一个我。
这一我,既不是肉体的我,又不是由社会关系中所见之群我,这是在此肉体我与夫由社会关系中所见之群我之外之一我。而此我,则只在我心上觉其有。而此所有,又在我心上真实觉其为一我。而这一种觉,则又是我心自由自在地有此觉。非由我之肉体,亦非由于外在之种种社会关系,而使我有此觉。此觉则纯然由于我心,因此可以称之为心我,是即詹姆士之所谓精神我。严格言之,有身体,未必即算有一我。如动物个个有体,但不能说动物个个有我。故必待有了社会我与精神我,始算真有我。但此二我相比,社会我是客我,是假我,精神我才始是主我,是真我。既是只有精神我得称为真我,因此也唯有精神我得可有自由。
让我举一显浅之例来证明此我之存在。我饿了,我想吃,此想由身我起,不由心我起。若由心我作主,最好能永不饿,永不需想吃。若果如此,人生岂不省却许多麻烦,获得许多自由?神仙故事之流传,即由心我此等想望而产生。又如我饱了,不能吃,此亦属身我事。若我身不名一文,漫步街市,纵使酒馆饭肆,珍馐罗列,我也不能进去吃。此乃社会我之限于种种关系之约束而不许吃。但有时则是我自己不要吃,不肯吃。此不要不肯,则全由我心作主,唯此乃是我自由。
此等例,各人皆可反躬一思而自得。兹姑举古人为例:元儒许衡,与众息道旁李树下,众人竟摘李充腹,独衡不摘。或问衡,此李无主,汝为何独不摘?衡答,李无主,我心独无主乎?在众人,只见李可吃,李又无主。此种打算,全系身我群我事,独许衡曾有一心我。
我们若把此故事,再进一步深思,便见在许衡心中,觉得东西非我所有,我便不该吃。但为何非我所有我便不该吃,此则仍是社会礼法约束。因此许衡当时内心所觉,虽说是心我,而其实此心我,则仍然是社会我之变相或影子,或可说由社会我脱化来。孔子称赞颜渊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一番颜渊心中之乐,则纯由颜渊内心所自发。此出颜渊之真心,亦是颜渊之真乐。如此始见真心我。若颜渊心中想,我能如此,可以博人称赏,因而生乐,则颜渊心上仍是一社会我,非是真心我。心不真,乐亦不真,因其主在外,不主在内故。此一辨则所辨甚微,然追求人生最高自由,则不得不透悟到此一辨。
以上根据詹姆士三我说,来指述我之自由,应向心我即精神之我求,不该向身我与社会我那边求。欧洲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曾分人生为三情状,其说可与詹姆士之三我分类之说相发明,兹再引述如下:
裴斯泰洛齐认为人类生活之发展历程,得经过三种不同的情状。首先是生存在自然情状,或说是动物情状中。此如人饿了要吃,冷了要穿,疲倦了要休息,生活不正常了要病,老了要死。此诸情状,乃由自然律则所规定,人与其他动物,同样得接受服从此种种自然之律则。在此情状中,人生与禽生兽生实无大区别。在此情状中生活之我,即是詹姆士之所谓肉身我。
裴斯泰洛齐认为人生由第一情状进一步转到第二情状,则为社会情状,又称政治情状。那时的人,也便成为社会动物或政治动物了。在此一情状下生活之我,则是詹姆士之所谓社会我。
自从人有了社会政治生活之后,人的生活却变得复杂了。吃有种种的吃法,穿有种种的穿法,甚至于死,也有种种的死法,较之在自然情况下生活的人,大为不同了。而此种种法,则全从社会外面,政治上层,来规定来管制,而且还有它长远的来源,这是一种历史积业。生活其中的人,谁也不得有自由。于是人在自然生活的不自由之外,又另增了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不自由。
中国老庄道家,是极端重视人生之自由的。他们因于见到人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种种不自由,乃想解散社会,破弃政治,回复人类未有政治和社会以前之原始生活。他们屡屡神往于人在自然情状下生活之可爱。但人在自然情状下生活,岂不更有许多不自由?因此他们又幻想出一套神仙生活来。在自然情况下生活的人,庄周称之为真人。在神仙境界中生活的人,庄周称之为神人。然而不为神人,亦难得为真人。因此无论神人与真人,则仅是些理想人,实际人又何尝能如此?
初期基督教,理想生活寄托在灵魂与天堂,关于人类在社会情况与政治情况下的一切生活,耶稣只说,凯撒的事由凯撒管,他暂时采取了一种不理不睬的态度。但那一种政治社会生活之不能满足耶稣内心之自由要求,则早在他这话中透露了。至于佛教,他们厌弃一般社会情况下的生活,是更显然的。所以他们要教人出家,先教人摆脱开家庭,继此才可摆脱社会和政治种种的束缚。
再说到近代西方为争取人权自由而掀起革命,这当然因于他们深感到当时政治社会种种现存情况之阻碍了自由。但他们之所争,实则只争取了人类自由之某种环境与机会,并不曾争得了人类自由之本质与内容。因自由只能由人自我自发,如所谓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岂不所争只是要政治和社会给与大家以言论与思想的自由之环境与机会?
至于言论些什么,思想些什么,则绝不是可以向外争求而得,也绝不能从社会外面给与。若使社会从外面给与我以一番言论与思想,此即是我言论与思想之不自由。可见言论思想自由,实际该向内向自己觅取,不能向外向社会争求。言论思想之自由如此,凡属人生行为之一切自由,实则无不皆然。若我们不明白这一层,则社会纵使给与我以种种自由,而我仍可无自由。故社会立法,至多可使我们不不自由,而不会使我们真有了自由。
现在我们依次说到裴斯泰洛齐所说的人类生活之第三级,即最高一级的生活情状,他称之为道德情状。他曾说:在我本身具备一种内在力量,这并非是我的动物性欲望,而且独立于我的一切社会关系之外。这一种力量,生出于我之本质中,独立存在,而形成了我之尊严。这一种力量,并不由其他力量产生,此乃人类之德性。他又说:道德只是每一人所自身具有之内在本质,道德并非来自社会关系。他又说:在道德力量之影响下,人不再感觉有一我,作为生活之中心,他所感觉者,则只是一种德性。在裴斯泰洛齐所认为不再有一我,而只是一种德性者,此种德性,实则犹如詹姆士之所谓精神我。而他所谓不再有一我作为生活中心者,此一我,则犹如詹姆士所谓之身我与社会我。
上述裴斯泰洛齐这番话,颇可与中国儒家思想相发明。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行仁义不足算道德。因在社会关系中,规定有仁与义,我依随社会之所规定而行仁义,则此种行为实出于社会关系,而并非出于我。只有由我自性行,因我自性中本具有仁义,故我自由性行,即成为由仁义行。此乃我行为之最高自由,此乃我内在自有之一种德性,因于我之有此德性而发展出此行为,此行为才是我自由的行为。即由我自主自发的行为,而非社会在指派我,规定我,亦非我在遵守服从社会之所规定而始有此行为。
照裴斯泰洛齐的话,人类生活,先由自然情状演进到社会情状,再由社会情状演进到道德情状,有此递演递进之三级。但人类生活,并不能过桥拔桥,到了第二级,便不要第一级。人类生活则只有因于进入了社会情状中而从前的那种自然生活的种种情状亦受其规范而追随前进,遂有所改变。又因于进入了道德情状中,而从前的那种社会生活之种种情状,亦再受其规范而追随前进,遂有所改变。而唯人类的自由,则必然须在第三级道德情状与精神我方面觅取之。人类因于有了此种精神我之自觉与发现,因于有了此种道德情状的生活之逐步表现出,而不自由的身我与社会我,也得包涵孕育在自由心我之下而移步换形,不断地追随前进,不断地变了质。
因此,人类之追求自由,则只有逐步向前那一条大路,由肉身我自然情状的生活进一步到达于社会我社会情状的生活,而更进一步,到达于精神我道德情状的生活,才始获得了我之人格的内在德性的真实最高的自由。我们却不该老封闭在社会关系中讨自由,我们更不该从社会关系中想抽身退出,回到自然情状中去讨自由。更不该连自然情状与这肉身之我也想抛弃,而幻想抽身到神仙境界与天堂乐园中去讨自由。
以上所说,或许是人人走向自由的一条正确大道。而中国儒家思想,则正是标悬出这一条大道来领导人的发踪指示者。这一条大道,再简括言之,则是由自然情况中来建立社会关系,再由社会关系中来发扬道德精神。而人类此种道德精神,则必然由于人类心性之自由生长而光大之。
因于此一大道之指点,人不该藐视由自然所给与的身我,因此儒家说明哲保身,又说安身立命。命则是自然所与而绝不自由者,但人能立命,则把不自由的自然所与转成为自我的绝对自由,而此一转变,则正需建立在自然所与上,因此儒家讲安身,又讲知命,再循次而达于立命。
若要安身保身,则必然须由自然我投进社会我。唯种种社会关系之建立,则应建立在人类之自心自性上,即须建立在人生最高情状之道德精神上。不能专为着保身安身而蔑弃了心性自由之发扬。当由人类心性之自由发扬中来认取道德精神,不该仅由保身安身起见而建立出社会关系,而遽认为服从那样的社会关系即算是人类之道德,或说是人类之不自由。因此儒家心目中之道德,乃确然超出于种种社会关系之上者,而又非必然脱出于自然所与之外者。若在自然所与之外来觅取道德,则必然会于肉体之外来另求一灵魂,必然会于尘世之外来另求一天堂,或说无我涅槃。而儒家思想则不然,因此儒家不成为一宗教。
又因此而儒家心目中之道德精神,必然会由人类之实践此项道德精神而表现出为社会种种关系之最后决定者。如是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凡属种种社会关系,皆将使之道德化,精神化,即最高的自由理想化。而社会关系绝然只能站在人类生活之第二级,必然须服从于人类生活之最高第一级之指示与支配。如是则恺撒的事,不该放任恺撒管,而大道之行,绝不在于出家与避世。
正因为儒家思想,一着眼直即瞥见了心我,即直接向往到此人类最高的自由,因此儒家往往有时不很注重到人类生活之外围,而直指本心,单刀直入,径自注重到人之精神我与道德我之最高自由上。当知人类尽向自然科学发展,尽把自然所与的物质条件尽量改进,而人类生活仍可未能获得此一最高之自由。又若人类尽向社会科学发展,尽把社会种种关系尽量改进,而人类生活仍可未能获得此一最高之自由。而若人类能一眼直瞥见了此心我,一下直接接触到了此精神我,一下悟到我心我性之最高自由的道德,人类可以当下现前,无入而不自得,即是在种种现实情况下而无条件地获得了他所需的最高自由了。于是在儒家思想的指示下,既不能发展出宗教信仰,而同时又不能发展出科学与法律两方的精密探检与精密安排了。
然则在中国儒家思想所用术语中,虽不见有近代西方思想史所特别重视的自由一名词,其实则儒家种种心性论道德论,正与近代西方思想之重视自由寻求自由的精神,可说一致而百虑,异途而同归。
无论如何,人类要寻求自由,必该在人性之自觉与夫人心之自决上觅取。无论如何,人类若要尊重自我、自由、人权、人生,则必然该尊重人类的自心自性,而接受认许儒家所主张的性善论。一切人类道德只是一个善,一切的善则只是人类的一个性。必得认许了此一理论,人类才许有追求自由的权利;必得认许了此一理论,人类才可获得自由的道路。否则若专在宗教信仰上,在科学探讨上,在法律争持上来寻求自由,争取自由,则永远将落于第二义。
一九五五年